这个年代,不仅文字被碎片化,连向来被认为简化思考的影像也被碎片化。文章要一句一分段,重点内容标红、加粗(某些领域类的文章我也认同这种做法,例如科普、法律等专业性文章),明说是服务读者,实则是不负责任地投喂,读者几乎失去了自行辨认和获取信息的空间,养成不留白、无需逻辑思考的阅读习惯;至于影像,充斥着三五秒内就要吸引人的短视频,大量夸张、失实、粗暴的信息填塞给了用户。
做媒体的人常把内容下沉挂在嘴边,但大部分时候,下沉的不是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而是情绪、欲望和暴力。识字让我们以为自己拥有知识、手握真理,下沉的内容让我们以为自己在阅读和思考,实际上我们陷入了大量无用信息组成的矩阵,用最狭隘的民族、权力心理,从中寻找认同。
当然,说着这种话的我,不见得比别人更有辨别力。我也是被时代车轮碾压,不知所措。回看2020年,疫情停滞了全球间的流动,中国电影独领风骚,但置身其中的人,心知肚明,创作和评论都面临最严峻的环境。更严重的话,我就不便直说了。
其实我只是想写一篇2020年个人观影的总结,却在开头三段说了一些虚头巴脑、不合时宜的话,能读到或者划拉到这里的人,也不容易。
去年初,封闭在家的两个月,感觉挺奇妙,定期出门买菜,大街空荡荡,像是电影里的末日景观。本来,我平常就是宅在家里,但失去出门的自由,和选择不出门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段时间,电影没有看很多,书也读不进去,被疫情和社会争论消磨了精力。
如果要选一部去年看完在我脑海里闪回了很久的电影,非法国片《悲惨世界》莫属。它跟维克多·雨果的同名小说没有关系,是一个现代城市中下阶层撕裂的寓言。“社会撕裂”这个词在互联网时代经常被提及。分化的信息和娱乐服务,加剧了传统社会的解体,人们只专注于自己关注的信息,只在意自己的权利,彼此割裂,等到谈论公共议题时,冲突大于共识。《悲惨世界》和《小丑》一样,都是讲受到打击/伤害但非正义的底层,奋起报复。

看《悲惨世界》时,我刚回到北京,正处于隔离期,所以看完这片,我首先想到的其实是中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导致的防疫和社会管理方式的不同。
西方国家普遍接受不能(短期内)绝对控制病毒传播的现实,防疫重点是维持医疗资源平衡,因此不过度干预人们的正常生活。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社会允许《悲惨世界》里的那种不稳定的社区存在,依然保障他们的权利。“造反”的孩子和被逼入绝境的警察,都成了加害者和受害者。它指向的问题不是孰对孰错,而是如何继续保持自由主义下的社会稳定。
中国讲究一切可防可控,为此不惜牺牲人们的自由和部分权利,即使不在疫情期,中国人也普遍愿意让渡出部分自由和权利,以换取理想的稳定。所以影片里那样的移民社区不会被允许在中国社会里明目张胆的存在。
去年打了五星的电影里,超过一半是和个体抗争,不向权力和命运屈服有关,例如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林权泽的《太白山脉》、保罗·格林格拉斯的《血色星期天》、艾伦·索金《芝加哥七君子审判》。这些影片让我感动的点也非常统一,就是对个体生命和力量的尊重。
《辛德勒的名单》的红衣小女孩,走在被德军残害的犹太人中,其他人都是黑白画面,只有她是彩色,让战争和人性抹上浓烈的荒谬色彩。《太白山脉》里,独立于战争之外的老师,清醒地认识到南北韩冲突的本质,只相信善良和正义,不从属于意识形态的任何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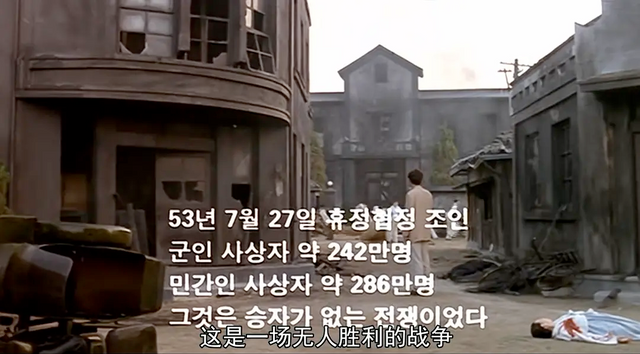
《血色星期天》让我感动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整个事件——争取民权,尤其是当军队失控,射杀游行者,把和平示威推向暴力斗争时,悲从中生。《芝加哥七君子》也是如此,被指控暴力示威的主角,代表同时受审的反战者,站在法庭上,放弃最后陈述求情的机会,念出从审判开始到结束,所有因对越战争而死的军人的名字。
另外还有两部电影打了五星,感动源于主角的漂泊感,无根生存的忧伤。这两部电影分别是许鞍华的《客途秋恨》和法斯宾德的《恐惧吞噬灵魂》。

《客途秋恨》中,晓恩在英国读完硕士,准备留下来工作,但被妹妹叫回去参加她的婚礼,不得不面对一直想逃避的母亲。母女俩说不上几句便会争吵,都想回避对方。丈夫去世,小女儿嫁人,母亲越发想念故乡,晓恩无奈陪她回了趟日本。在母亲的故乡,她体会到了母亲曾经的举目无亲的孤独感。回到香港,晓恩在电视台忙于工作,收到身在内地的爷爷中风的消息,母亲帮她收拾行李,叫她无论如何回去看望爷爷。三代人,归属于不同的土地,时代有别,那份乡愁和亲情在相聚别离中,隐隐流露。
今天个人时间有限,先更新这么多,明天接着写。。。。
大家腊八节快乐!附上我今天的早餐:腊八粥

你们吃腊八粥没?
这是篇抄袭剽窃自其他网站的文章,一字不漏的抄袭!原文地址:https://www.douban.com/note/791754075/
Downvoting a post can decrease pending rewards and make it less visible. Common reasons:
Sub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