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一个记忆天才能够记起一生经历的每个细微末节。想必你会认为,此人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然而恰恰相反,他非常不幸:每时每刻都有无数记忆中的旧事涌上心头,让其不堪其扰。幸好一般人多半不是记忆天才。常人多半不必为记得太多而烦恼:可能闯入记忆中的大多数东西,都因人脑的选择而被挡住了。那么,选择性记忆仅仅是人类的幸运吗?它还可能有哪些利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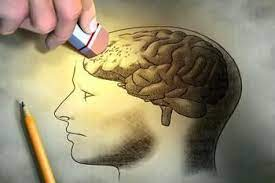
别记得太多
中学生大概都知道如下故事:有人请教爱因斯坦,音速是多少?爱因斯坦告诉他:你到书上自己查去,我从不记这类很容易查到的东西!这种说法或许有点极端,我不能肯定是否真的出自爱因斯坦。但在基本精神上,我不能不持同样的观点:不能也不必记太多的东西,以免压垮大脑的记忆系统!
只是你会说,得首先解决一个难题:如何选择那些需要记住的东西呢?其实,你多半不会遇到这样的困扰。人生从开始记事时起,就会无意识地、本能地完成无数次选择:记住那些需要记住的东西,忘记那些不很需要的东西。这种选择能力来自于人类的进化,正是进化让我们获得一种保护机制,随时从大脑中删除那些不常用的信息,以便腾出尽可能多的空间,好容纳其他更有用的信息。
第一个难题就这样由生物学解决了,并不劳我们费神。实际上,大多数人甚至不会意识到,竟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然而,生物学并没有彻底解决记忆的选择,它还是将一小部分选择遗留给了人类,让人们去有意识地完成。这样,所谓选择性记忆就由两部分组成:无意识选择与有意识选择。只有后者才进入我们的关注。我们终究保留了一点“自主权”,这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个难题。如何选择记忆并非天生就会,这需要学习!天生就会的只是无意识选择。
不过,倒也不必因此而烦恼。在着手应对“选择记忆”这一难题时,至少有一些强有力的理由让你稍安勿躁。一,人类毕竟主要依赖于无意识选择,这叫做懒人多福!如果没有十分的必要,不妨根本不去考虑选择问题,随性而已。大多数天下人岂不正是这样悠闲度日,也不见得潦倒不堪。二,有心人只注重选择原则,而不是选择事项。例如,你不妨给自己定下原则:尽可能记住世界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与自然、人文概况;也全力记住世界历史上最重要事件的发生年份。这相当于:通常不是选择记住哪件特定的东西,而是选择记住某些装东西的“抽屉”。三,有诸多记忆的辅助手段可用:手册、笔记、日记、索引、记事录等等。
“不记太多”,不仅是一条生活原则,也是一种人生智慧。
作为生活原则,它首先是帮助你处事。每天遇到的事形形色色,如果每件事都在你心中翻腾,放不下来,一定不堪其扰。你可能且一定会忽略许多事,或者根本视而不见;唯有如此,才可能抓住几件最不能疏忽的事情。
作为人生智慧,它敦促你清除许多引人烦恼的记忆。没有人能忘却每件不愉快的事;但如果你记着每件伤心事,那么你就不可能有快意人生了。
有意识忘却
选择了记忆,也就选择了忘却。别老惦记着生物学家告诉过你:一个人有多少多少亿脑细胞;这种知识无助于你的记忆。更靠得住的是来自经验的结论:你压给自己的记忆任务越重,需要忘却的东西就越多。有意识地忘却,将让你受益无穷;就正如我们每天都要从电脑中删除掉许多东西一样。
你忘却了哪些东西?这听起来有点像一个笑话:能够谈论的忘却就不是真正的忘却!因此,要紧的与其说是忘却什么事项,还不如说是忘却的原则——这与选择记忆时的考虑几乎是一样的。例如,不妨确立这样一条原则:忘却大报的全部头版内容吧!
诸如此类的原则,在一生之中会要积累很多。例如:忘却进入你眼帘的所有(或大部分?)广告;忘却不重要会议通讯录中的全部人名;忘却俄罗斯小说中那些长而难记的人名;忘却每次宴会的祝酒词;忘却所有大人物的讣告……。该忘却什么,当然因人而异;我应忘却的东西,并非恰恰是你该忘却的。就我而言,这样一个忘却的清单真的很长很长;丢掉了这样一个长长的包袱,我会如释重负!谁不想活得更轻松?
在我的老同事中,就有这样的记忆天才:他能背诵《红楼梦》中的所有诗词;能记得《镜花缘》中那些境外奇花异草的名字;记得1955年授衔的全部将帅;记得民国年间的所有影星……。我非常佩服此人的惊人记忆力。尽管如此,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忘却所有这些东西,并非它们毫无价值,而是因为我不想因此而劳神。
如果有人说:这不过是记不住的托词而已!我也不想反驳,因为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我也能记住那么多。但我确实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体会到:有意识地忘却一些东西之后,就可能记住一些更感兴趣的事物。例如,我就能记住中国史与世界史上主要事件的年份;或许有人认为这很不值,但我觉得这总比记住一些无聊文章更有价值。
良性选择
“记住历史大事的年份”,真的是一个合理选择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当然不会有也不应有统一答案。我愿意选此,那只是我的个人偏好;如果是另一个人,完全可能嗤之以鼻,我没有任何理由说他不知轻重。
可见,选择记住什么,完全是个人的权利,他人无权置评。如果说,此处还有什么共同的原则,那就是:每个人的选择都应当是理性的,这意味着选择你认为该记住的东西。这样的选择,我称之为良性选择。良性选择的标准肯定随人而异;否则,选择记忆就不是一种个人权利了。
良性选择的概念似乎包含着悖论:我选择记忆的东西,肯定是我认为该记的;因此,我的记忆选择就自动地是良性选择;非良性的选择并不存在,良性选择一词就没什么意义了!不过,上述推理包含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前提,即每个人都有一个前后一贯的标准,借以决定他的良性选择。然而,这样的假定相当于:认定每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就没有自相矛盾的时候;而现实中的个人却往往不是这样。
例如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我不能不记住每一条“禁言”的规矩,这就成为我的记忆选择中的一个良性选择。但这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种自律的原则而已,并不能保证绝对遵守它;无论如何,我还没有修炼到能够完全慎言的程度,并不保证自己完全没有放言无忌的时候,以致不时惹出一些麻烦来。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否定,在选择记忆时我确实坚持良性选择这一原则。
有什么良性选择的普遍经验吗?我想世界上应当没有这种东西。不过,我还是愿意举出一个例子,它颇能说明问题。
如果某人夜行跌倒于某坑中,那么他在一段时间内会牢牢记住那个该死的坑,警告自己绝不可再掉入那坑中。不妨称之为避坑记忆,选择这种记忆肯定是良性选择。这种选择的价值比初看起来要大些。一般说来,刚刚受到挫折的人,那个让其受挫的陷阱,是特别需要记住,不能重蹈覆辙的。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大智慧,但人们恰恰容易忘记眼前的教训,经常跌倒在同一坑中。今天那些刻意美化文革的人,无疑已不记得“十年浩劫”中坑人无数的那个坑了!
这样,选择记住即时教训,就是一种良性选择。
恶性选择
与良性选择相反,恶性选择恰恰记住那些不该记或者不必记的东西。当然,此处的所谓“恶性”仅仅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并不涉及对记忆内容的价值判断。
首先考虑一个特殊例子。统计学家的大忌,就是偏好记住许多孤例。对于已被确证的统计结论来说,任何孤例——无论它支持还是反驳统计结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一种关注孤例的偏好,除了妨碍依赖理性论证的统计思维之外,别无价值。对于这些孤例的记忆与广泛传播,就是一种恶性选择。人们大概都还记得,一位大人物最爱讲“老大粗”的成功故事。我记得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讲话,其中列举了颇有成就的古今中外名人,他们全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接近于就是“老大粗”,例如刘邦、赵匡胤、朱元璋、李自成等等。他要论证的观点无非是:要成大事,实在不必读很多书。至于这一主张最终被发展成一种理论——知识越多越反动,那是后话。
同样的逻辑还盛行于类似的事例中。当下最触动国人神经的是中医。自1920年代以来,中西医共存的局面维持已久,大体上能够相安无事。但当政治强势介入之后,就无法假装“天下本无事”了。既然“保中医”就是“保民族传统”,谁还敢要求中医药进行“双盲实验”?既然没了双盲实验这种举世公认的检验方法,靠什么证明中医药的疗效呢?那就是沿用数千年的传统方法:举例证明。只要说张三李四被什么药治好了,那个药就可以放行了!
一旦这一古老智慧在某一领域被认可,那么推广至其他领域就畅通无阻。于是我们的国粹中就增加了一条:以点带面!凡是在点上成功的东西,也就获得了“面上”的通行证。这样,陈永贵的大寨经验成了全国的样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成了全国的榜样;最近又有什么“枫桥经验”很快要推行全国了……。
这种智慧的妙处就在于:要证明什么吗?请举例吧。凡有例为证者都行!那么,要记住什么呢?例子而已!而全部人类经验所提示的恰恰相反:孤例不足恃!与其让一些人去鼓动人们记住孤例,我宁可鼓动人们忘却孤例。当然无须否认,孤例并不失说明问题的价值。
选择记住那些证明不了什么的孤例,就是一种恶性选择。
在这种意义上,孤例是不该被记住的东西。我不能不坦然承认,这种似属极端的选择原则,未必能被大众接受。其实,大众是否接受并无太大的重要性。真正令人忧虑的是,时值21世纪,仍然有不少知识精英在依靠举例进行论证,没有多少人进入某种最低限度的统计思维!我不知道,这种状况如何适应一个大国的科学雄心。
历史记忆
国家、民族、社会甚至个人的许多故事,都被保留在历史中了。这样,历史就成为一种民族记忆。民族记忆是一种群体记忆,当然不同于个体记忆。但是两者之间仍然有许多类似之处。就本文的思路而言,首要的问题是记忆的选择。
不同于个体记忆,历史记忆有一些显著特点。
首先是选择性更强。原则上,汇成民族记忆的每一个别史料都有其价值。但是可以肯定,你家阿三的婚丧娶嫁多半进不了《现代中国史》,历史只能大幅度地忽略掉许多东西,让剩下的东西能够被浓缩在某个详略适中的文献之内。
其次是记忆的主体是无比复杂于个体的群体,群体如何体现,肯定是一个高度争议的问题。如果认定国家记忆就是官方记忆,肯定会遭到大量民间记忆者的反对;如果认为国家记忆是民间记忆的某种综合,综合的有效性肯定会遭到强烈的质疑。当下的问题,恐怕主要还不是质疑官方主导国家记忆,而是民间记忆应当适当地体现在国家记忆中,不致听任其完全湮没无闻。官方应当有高度的责任协调各个社会阶层;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只能撕裂民族的整体记忆,最终让本应保存于民族记忆中的亮光荡然无存!如果像今天这样,存在着截然对立的两种抗战史、两种文革史、两种改革开放史、两种抗役史,我们将如何面对司马迁、司马光等伟大先贤呢?
还有,民族记忆必定面临着如何与人类记忆承接的问题,而这就密切联系于国家如何融汇于人类的主流文明。一个被世界大多数民族视为另类的民族,如何能指望,自己的民族历史将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适当位置呢?我们总不能永远让自己的孩子学习这样的世界史: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心在延安;1950年联合国侵略了朝鲜;1991年美国的阴谋摧毁了苏联;2001年摧毁世贸大厦的沙特人是反美战士;乌克兰人不投降俄罗斯妨碍了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