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的读者或许有几分喜爱乌托邦;但对于在惨烈的社会实验中涌现出来的乌托邦,恐怕令大多数人都谈虎色变。这一不幸事实的历史后果是,对于任何高调宣扬但前景难测的宏大社会计划,人们都不免心存疑虑。不过历史仍然提供了实施社会计划的若干成功案例。本文将这种成功的范例,称为“现实的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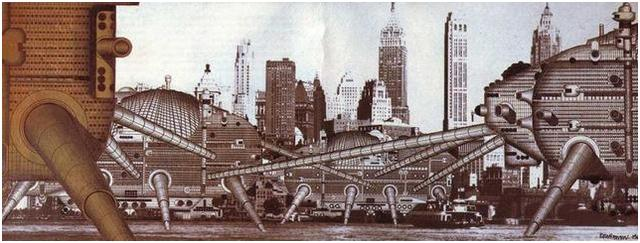
罗斯福新政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哪个国家最不喜欢国家计划,那么肯定是美国了。美国的国家信仰,恰恰是国家主义的反面——个人主义。靠国家来为你规划一切、提供一切吗?别想!自己想办法去吧。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迄今都没有完全实现医疗福利保障的国家。就为此事,川普与奥巴马、拜登的争执还没完呢。
如此说来,美国岂不是最典型的自由放任国家了?但恰恰就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诞生了文明史上最伟大的社会计划之一,它就是举世皆知的罗斯福新政。没错,正是那个受全世界敬仰的二战领袖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32任总统,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连任4届总统的人。他在其任上做的两件大事就是:推行新政与领导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他名垂青史!
极端的自由放任国家推行最伟大的社会计划——实在太矛盾了!要理解这一点,对美国这个国家的特质要有更深入的了解。从根本上说,美国就是一个存在于一系列矛盾中的国家。它只有最短浅的历史,却继承了历史最悠久的西方文明;它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弱化国家权力,却拥有世界上最忠诚的爱国者;它由国家主持了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却不拥有一所国立名牌大学,也没有一个实体性的科学院;它具有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却有西方国家中最差的社会福利;它拥有世界上最富有的国民,却有一个捉襟见肘、负债累累的政府;它在重大国际行动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强大国力,却无力解决微不足道的社会治理问题;它在“马歇尔计划”之类的国际行动中慷慨无比,却在许多事情上一毛不拔;它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政府预算,却在许多政府开支与社会开支上异常吝惜;它维护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却拥有世界上最慷慨、人数最多的慈善家;它的选举政治拥有最欠缺君子风范的政客,却具有大概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
如果你知道了这一切,对于罗斯福那个似乎反传统的新政,就不致特别奇怪了。
简单说来,罗斯福新政就是在大萧条的1933年开始实行的经济复兴计划;其中包括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实行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核心的经济政策是所谓“三R新政”,即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改革(reform)。一些具体措施包括:调整银行与金融系统;大幅度加强国家对工业生产的宏观调控;实行某些农业干预政策;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问题。
罗斯福新政是一项异常庞大复杂的社会计划,牵涉极广,具有深远的影响,其错综复杂的后果颇难评价,迄今仍有争议。它缓解经济衰退的短期效果似乎得到广泛认可;长期效果就比较复杂,难以权衡其利弊。普遍认为,新政铸造了现代美国政府的权力架构,更新了传统的国家观念,显著扩张了行政权力,提升了社会福利设施。继承这一切的,既有罗斯福的民主党同道,也包括许多反对派,因而不能不说,新政成为一项国家遗产!
欧洲福利社会
欧洲是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摇篮。但在许多人看来,欧洲今天的表现不佳,似乎再也不是世界的样板了。不过,至少在社会福利这一点上,欧洲仍然享有世界最高声誉,其他地区难以与之比肩。
自上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引领着西方的工业化潮流,在各个领域,欧洲都深受美国影响。罗斯福新政不可能不直接地(通过马歇尔计划)或间接地影响着欧洲的社会政策。不过,我宁可认为,欧洲之所以有今天这种形态的福利社会,主要是欧洲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外来因素的影响仅有次要的作用。
对于欧洲福利社会,已有广泛的报道,一般人都有所了解;曾在欧洲旅游或者居住者,自然了解得更详尽。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那句已成经典的名言:
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护!
如全世界普遍认为的,这一切在北欧做得最好,乃至有人称之为今天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人会忍不住立即评论:这不就是人类向往已久的人间天堂?是否为天堂的问题暂不置论,仅仅关注: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我认为不妨使用三个词:意愿、财富、制度。
意愿源自一种最普遍的社会共识:国家的发展应当以实现共同富裕、普遍幸福为目标。这种理念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与普济理想、近代的乌托邦幻想、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追求、19世纪工人运动的呼吁、以俾斯麦为首的德国社会福利计划的理念,等等。到20世纪,对于社会福利的普遍要求,成了无人置疑的社会公理。这就使所有主张并争取社会福利的政党,在政治上具有理所当然的道义优势,而反对者则逐渐绝迹。
财富源于社会生产的空前增长;而后者又来自市场经济制度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到1960年代,欧洲已成为空前富裕的社会,普遍的富裕生活不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现实:如果不普遍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个日益产能过剩的社会哪来出路?
制度保证源于欧洲数百年的社会与政治进步。其一是民主制度的逐渐完善,使得居民的意愿能被充分表达;其二是国家在其历史继承中获得的强势执行力,而这对于一个实行集中式社会福利计划的政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三件东西实际上就是:福利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福利主义提供了意愿,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提供了财富,民主制度提供了福利政府的执行力。没有这三件东西,福利社会只是一个空中楼阁;一旦具备了这三样东西,社会本身的逻辑就会推动社会福利计划的实行。可见,20世纪欧洲福利社会的到来,绝非偶然,更不是某几个救世主的恩惠,而是西方文明在其现代演进中的逻辑后果。
1990年代,日裔政治哲学家福山石破天惊地提出了“历史的终结”。我不免寻思,福山的结论或许应当修改为:历史已经并将终结于欧洲福利社会!
亚洲之星
“社会计划”的理念源出于西方,在亚洲的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如果也出现了成功实现某种社会计划的“亚洲之星”,那么,一定是某种西方理念传入的结果。但是,亚洲有其特殊的历史传统与精神价值,因此,“亚洲之星”必不同于前面所述的西方事例。
中国、日本、韩国等等都可以作为“亚洲之星”的例子。不过,下面选取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即所谓“亚洲四小龙”,或许更具典型性。在1980年代,四小龙曾经红极一时;今天似乎已经褪色了,以致不知该如何重新确定称呼。这与其说是因为四小龙不行了,事实上“龙已非龙”,还不如说是周边一些国家有样学样、迎头赶上了。不管怎么说,今日四小龙仍然生龙活虎,虽然香港这一特例有点例外。不过,此处不去全面评价四小龙的得失,仅仅介绍它们在实行社会计划方面的某些特点。
韩国今天仍然是光彩夺目的明星,其经济总量雄踞大国俄罗斯之前,其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2019)。具有这种发达程度的国家,就不必再与他人比块头了,那东西只在低水平下才说明问题。现在韩国看重的是顶尖技术、世界级大公司,二者它都不缺少。韩国之所以有今天,得感谢一个人,他就是前独裁者朴正熙。他领导的军政府,在韩国实行国家操控的工业计划;这项计划培植了现代、三星、大宇等产业大鳄;正是这些巨无霸,奠定了韩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你想必听说了:三星正在制定最具雄心的发展计划,旨在未来几年内夺取世界芯片技术之冠!
台湾曾经是蒋氏父子内战失败之后的栖身之地,在1950年代没有人看好其前景。强势而又勤政的蒋经国,恰似韩国的朴正熙,他那朴实且坚毅风格的领导,扎实打造了台湾的工业化基础。蒋经国在台湾重点推行所谓“十大建设计划”,其中尤其包括于台湾现代化极其重要的环岛高速公路建设。曾经在苏联接受过红色训练的蒋经国,在台湾推行的建设计划颇具红色风格,而且也用了类似于大陆的人海战术与精神激励;蒋经国本人更是身先士卒,完全以普通劳工的姿态与工人吃住一起。我在台湾旅游时,在许多工程纪念地看到当年筑路者的艰苦奉献与巨大牺牲,不能不为之动容!想当年蒋经国只身困在西伯利亚,何曾料到自己的抱负竟然实现于一个海岛之上!
新加坡不过弹丸之地,当然无法施展如韩国台湾那样的计划。但新加坡同样依赖于一个强人,他就是比朴正熙、蒋经国更老谋深算的李光耀。新加坡固然无需规划重大工程,但它在夹缝中求生,需要更高的生存机巧。在外交策划、产业布局、金融对策、人口计划、居民安置等等方面,都需要精细的考虑,而李光耀及其亲信,恰恰擅长于此。只有在新加坡这样狭小的土地上,任何施政计划才真正成为一种完全的计划性运作。因此,新加坡的社会计划完全是货真价实的。
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对于香港的情况就只能从略了。
乌托邦的现实性
已经见证的这些社会计划是乌托邦吗?这得首先界定乌托邦这一概念。
自从莫尔虚构了他的理想社会的故事之后,这一类的虚构就层出不穷,引人入胜。后来,乌托邦故事又启发了一些社会的改革者与建设者,他们以现有社会作为试验基地,依据自己的理想,提出某种理想社会的蓝图,然后制定计划,循此计划去改革或建成蓝图中的社会。这样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理想的计划,自然就被称为乌托邦。正式地说就是:
依据某个社会计划,改革或者建成某个理想社会,谓之乌托邦。
乌托邦首先指那个希望达成的理想社会,同时也指达成理想社会的计划与实现过程,两者无需严格区别。乌托邦的现实性,就是其中那个理想社会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可能性的大小亦即现实性的高下。有最大现实性者,乌托邦必定实现,习惯上人们将不再称之为乌托邦;有最小现实性者,乌托邦必不可能实现,最终不免成为纯粹的空想。其他乌托邦则介于以上两者之间,其现实性愈高,就愈有理由被称之为现实的乌托邦。
罗斯福新政所要建成的理想社会,至少要实现如下目标:消除主要的危机症状,如破产、失业等等;让经济活动在宏观上得到适当控制;恢复经济的增长活力。欧洲福利社会的目标是:将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包括生老病死、基础教育、医疗保护、失业保护等等)定出最低标准,并纳入政府的管理;福利成本由个人、市场与政府分担;政府分担份额渐次增大,直至担其全额。亚洲四小龙的社会计划的目标各有不同,此处不赘。
罗斯福新政、欧洲福利社会、四小龙的社会计划等等,其结果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计划者的最初理想。在这种意义上,它们都可称之为“现实的乌托邦”。但在各个不同情况下,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程度就大有区别,因而其现实性也就各异。四小龙的社会计划主要侧重于近期建设目标,理想化成分最小,现实性最高,因而最少乌托邦色彩;或者说,是最现实的乌托邦。欧洲福利社会是一个高度综合性的社会改造计划,其众多的具体目标都不免高度理想化的成分,是否已经或者可能完全实现,不能不引起持续不断的争执。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欧洲福利社会计划最少现实性,因而最可能被讥为乌托邦!至于罗斯福新政,则不妨认为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不过,今天对于新政的关注已渐渐消逝于无形了。
尽管如此,尽管欧洲福利社会的完全实现仍然任重而道远,却不能不说,这是人类历史上一项最伟大的事业,是让历代先贤莫尔、欧文、圣西门、蒲鲁东、拉萨尔、俾斯麦、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等能够含笑九泉的伟大社会进步!仅是这一点,你就不致对“社会计划”取完全的否定态度了。